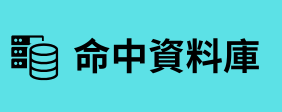法院似乎将示威活动视为上述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持续武装冲突的一部分。法院进一步分析了以色列国防军交战规则中列出的三种不同类型的目标。第一类是哈马斯成员,。法院认为,这些人积极参与敌对行动,因此可以根据其在“积极敌对行动”范式下的身份成为攻击目标(Hayut 院长,第 11 段)。正如科恩所提到的,法院饶有兴致地避免直接援引其在著名的“定点清除”案(反酷刑公共委员会诉以色列政府案,HCJ 769/02)中发展起来的“持续作战职能” ,但多次深入提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直接参与敌对行动”概念的解释性指导(Melcer,第 45 段)。然而,反复提及大多数遇害示威者是哈马斯军事派别成员,多少暗示了类似的做法。然而,以色列国防军的《交战规则》显然包含针对另外两类人员的指示:a.) 示威活动的领导者和核心煽动者;b.) 其他示威活动参与者。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规则
这些“核心煽动者”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精确射击腿部”予以制服。法院似乎接受了这种做法,尽管哈尤特院长在其同意意见中承认,这种对“核心煽动者”的特殊待遇在国际法上没有依据(哈尤特院长同意意见,第12段)。然而,法院强调,在执法模式下使用致命武力必须始终保持适度,并且只有在对生命或身体完整性存在真正危险的情况下才可接受(Melcer,第 40 段)。尽管这些声明乍一看意味着使用致命武力的条件与国际人权法实际要求的条件相同,但下面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存在
法院多次指出,允许使用致命武力的威胁必须是“即时的”或“迫在 欧洲数据 眉睫的”(Melcer,第46段)。然而,法院未能证明这种即时性确实存在。Melcer法官指出,哈马斯的意图是煽动群众突破安全围栏,进而袭击以色列士兵和平民(Melcer,第54段)。鉴于这些论点,只有在围栏实际被突破后,才会构成对生命和肢体的威胁。另一方面,法院似乎认为安全围栏被突破本身就构成了足以允许使用致命武力的威胁(Melcer,第56段;Hayut总统,第6段)。然而,围栏被突破与对以色列平民或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生命和肢体的实际伤害至少存在一个因果关系。
上述威胁尚未完全实现
(Melcer,第55段)。因此,与其自身关于立即性要求的理念相反,本法院 卫星互联网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似乎接受了被告方的论点,被告方认为,在威胁实际发生之前,可以某种程度上预防性地使用致命武力予以应对(参见上文埃利亚夫·利布利希 (Eliav Lieblich) 的案例)。为了支持这一论点,本法院援引了先前的判例法,例如在“ Al-Masri诉军事检察长案” (HCJ 15/1971)中,该案处理了类似的情况,即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2011年“灾难日”(Nakba day)之际向试图跨越以黎边境的巴勒斯坦抗议者开火,以及“Anconina诉首席军事检察官案”(HCJ 88/48)。然而,这种紧 购买电子邮件列表 迫性的定义显然与国际人权法的要求不相一致(法院似乎从一开始就否认其适用)。这意味着法院援引的“武装冲突法执法范式”下的“迫在眉睫的威胁”要他们在抗议活动 求必须以某种方式与国际人权法不同的方式来解释。